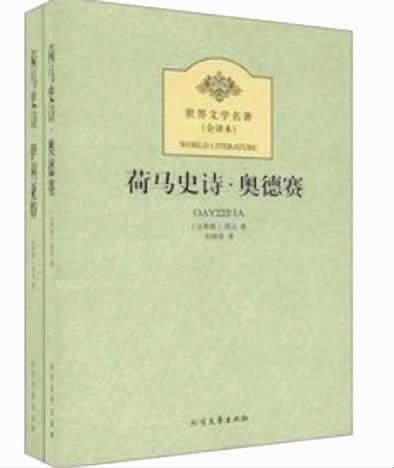
《荷马史诗·奥德赛》
当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文学将永远具有生命力。
小说比电影的优势在哪里?电影在哪些地方比不过小说?这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更是对我所在的中文系师生们生死相关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核心主导艺术样式和载体,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在19世纪的西方发展到巅峰,到了20世纪,电影的风头显然盖过了小说,成为最强势的艺术媒介。电影一出现,人们就预言它会让小说退出舞台。2003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一门“中国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的课,11个人选修,其中9个是研究电影的。美国大学里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连研究著作都难以出版,只好把文学的课题拼命往“文化”上靠。
电影不可抵挡的魅力,其实用一句俗话就能概括:百闻不如一见。人所有的感觉器官中,视觉的冲击力最为强劲。因为从进化的角度,视觉与人类的生存最密切相关。在原始的丛林里,最决定我们前辈生死的,是视觉,这个本能已经刻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对这些本能不那么需要的时代———因为基因的变异需要漫长的时间。

《傲慢与偏见》
但是,电影/视觉最强势的地方,也就是它最弱的短板。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本能最强大,但本能也是最盲目的和最底层的。在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以及理性的表达,虽然看上去抽象、脆弱而枯燥,但却是人类不断提升的关键。
举几个例子:
电影崛起的最大动力是视觉性,但这个动力已经衰竭,无论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电影最大的软肋是交互性,因为电影有很强的线性,你没法在电影院里暂停、跳转,而这方面游戏是强项。
电影最大的限制是3小时长度,以往的大师们为此呕心沥血,戴着脚镣跳舞,避短扬长,甚至化短为长,令人钦佩。但是,局限依然是局限。有多少小说改编成电影不会遭受信息损耗的?而新的艺术媒介提供了更广阔的时空。
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沉浸感,几乎借此完胜文学。但是,现在出现了远比电影更有沉浸感的艺术媒介,你可以走进去,这就是VR。
换句话说,电影这个媒介,正是因为它的先天不足而正在遇到比电影更新的媒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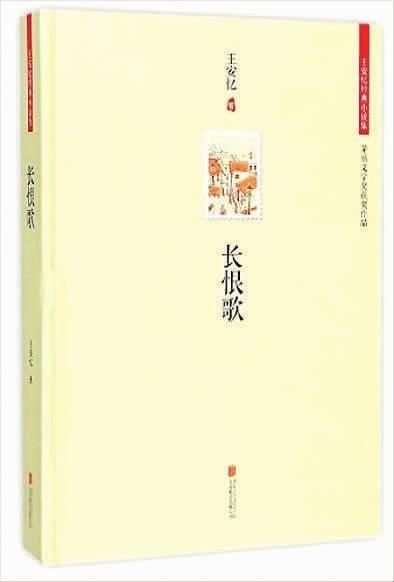
《长恨歌》
那么文学又有什么长处?
19世纪,著名画家特纳参观新发明的摄影展览后,长叹一声:绘画完蛋了。但绘画没有完蛋,而是通过塞尚等走向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抽象与主观的道路。20世纪,托尔斯泰看到摄影机后,感叹文学将从此改变。但文学没有完蛋,文学在逼真再现世界方面无法与电影竞争,就更加注重开拓内心世界,以及幻想世界。
王安忆说过,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美国文学批评家卡米拉·艾略特说“好书难成好电影”。文学经典电影化的困难堪称有目共睹。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长期以来阅读经典小说时在头脑中形成的人物形象,与屏幕上视觉形象的严重不符。其实这不能怪导演和演员,这是影视的原罪,文学的荣光。
当年鲁迅就曾经在《论照相之类》中对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有过酷评:“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象一个麻姑。”现在人会觉得鲁迅太刻薄,对国粹京剧和梅兰芳本人有偏见。但是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对视觉表演艺术的不屑,对自己老本行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一个《红楼梦》粉丝对自己偶像的忠诚。
梅兰芳自己也谈到红楼戏难演:“前清光绪年间,北京只有票友们排过红楼戏。那时票房的组织还没有后来那么普遍发展。著名的有两个票房,一个在西城,叫‘翠峰庵’,名角如刘鸿声……他们排过‘葬花’和‘摔玉’。陈子芳扮黛玉。他的扮相是梳大头穿帔,如同花园赠金一类的小姐的打扮……每逢黛玉出场,台下往往起哄。甚至于满堂来个敞笑。观众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林黛玉……可是内行看了这种情形,对于排红楼戏便有了戒心。”
荷马史诗中写海伦的美,就说那些特洛伊德高望重的长老,本来对这个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女子充满怨念,但是他们在城头一看到海伦,就觉得为她打一仗也是值得的。再看看电影《特洛伊》中的海伦,那简直就是五大三粗啊。
我是个金庸武侠小说迷,但每次我看所谓的武侠电影里那些大侠们的死缠烂打,贴身肉搏,气度全无,犹如街头混混,都是无比失落。武侠小说是最需要打开人的想象力让人飞翔的,但这想象力投射建构的对象,一旦转换为银幕上的具象,就立刻跌落尘埃,猥琐暗淡。这可以称为武侠神髓的不可视化。
麦克卢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概念: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他认为文字相对于电影而言,属于低分辨率。低分辨率在这里不是贬义词,文学的低分辨,就像中国传统画的留白和写意,为欣赏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屏幕的形象固然直观生动鲜明,但语言创造的形象却更含蓄,更灵活,更能激活个体的想象力。“嘤咛”一声,需要多少高的比特率、采样位数和采样率才能表现?“吹弹得破”四个字,要用多高的分辨率才能表现?
那些电影难以表现之处,就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即使是在追求互动性的新媒体时代,文学也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当传统艺术中被压抑的交互性被技术激活释放,成为人民群众越来越大的渴望,缺乏交互性就会成为艺术的软肋。游戏的确比电影能带来更多玩家的选择,但文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能提供更高层次的互动———想象的互动。
文学不死,只是转型。人类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自己常用的一切媒介、符号和工具美学化、艺术化,也就是升华———用哲学的说法,就是异化。比如声音就升华成音乐,图像就升华成美术,哪怕是最实用的手机,也会不断增加超功利的审美因素。那么,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也就还会不断地升华语言,把语言艺术化,也就是文学化。电影电视的出现,反而让文学变得更加纯粹,并将继续成为影视、游戏、VR的灵魂。外壳可换,灵魂不灭。
(作者严锋,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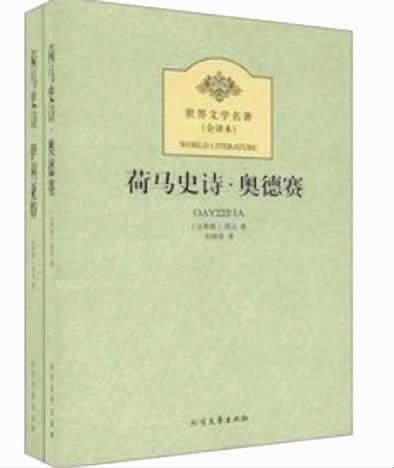
《荷马史诗·奥德赛》
当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文学将永远具有生命力。
小说比电影的优势在哪里?电影在哪些地方比不过小说?这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更是对我所在的中文系师生们生死相关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核心主导艺术样式和载体,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在19世纪的西方发展到巅峰,到了20世纪,电影的风头显然盖过了小说,成为最强势的艺术媒介。电影一出现,人们就预言它会让小说退出舞台。2003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一门“中国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的课,11个人选修,其中9个是研究电影的。美国大学里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连研究著作都难以出版,只好把文学的课题拼命往“文化”上靠。
电影不可抵挡的魅力,其实用一句俗话就能概括:百闻不如一见。人所有的感觉器官中,视觉的冲击力最为强劲。因为从进化的角度,视觉与人类的生存最密切相关。在原始的丛林里,最决定我们前辈生死的,是视觉,这个本能已经刻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对这些本能不那么需要的时代———因为基因的变异需要漫长的时间。

《傲慢与偏见》
但是,电影/视觉最强势的地方,也就是它最弱的短板。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本能最强大,但本能也是最盲目的和最底层的。在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以及理性的表达,虽然看上去抽象、脆弱而枯燥,但却是人类不断提升的关键。
举几个例子:
电影崛起的最大动力是视觉性,但这个动力已经衰竭,无论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电影最大的软肋是交互性,因为电影有很强的线性,你没法在电影院里暂停、跳转,而这方面游戏是强项。
电影最大的限制是3小时长度,以往的大师们为此呕心沥血,戴着脚镣跳舞,避短扬长,甚至化短为长,令人钦佩。但是,局限依然是局限。有多少小说改编成电影不会遭受信息损耗的?而新的艺术媒介提供了更广阔的时空。
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沉浸感,几乎借此完胜文学。但是,现在出现了远比电影更有沉浸感的艺术媒介,你可以走进去,这就是VR。
换句话说,电影这个媒介,正是因为它的先天不足而正在遇到比电影更新的媒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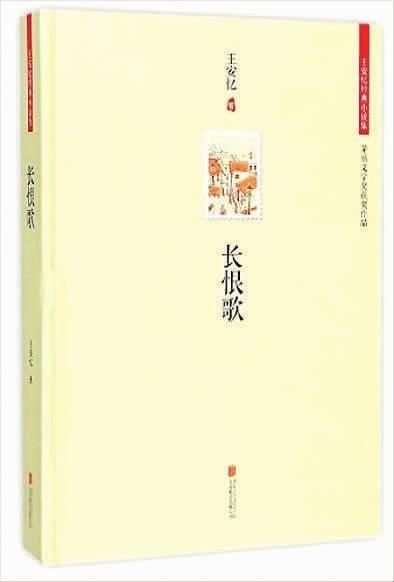
《长恨歌》
那么文学又有什么长处?
19世纪,著名画家特纳参观新发明的摄影展览后,长叹一声:绘画完蛋了。但绘画没有完蛋,而是通过塞尚等走向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抽象与主观的道路。20世纪,托尔斯泰看到摄影机后,感叹文学将从此改变。但文学没有完蛋,文学在逼真再现世界方面无法与电影竞争,就更加注重开拓内心世界,以及幻想世界。
王安忆说过,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美国文学批评家卡米拉·艾略特说“好书难成好电影”。文学经典电影化的困难堪称有目共睹。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长期以来阅读经典小说时在头脑中形成的人物形象,与屏幕上视觉形象的严重不符。其实这不能怪导演和演员,这是影视的原罪,文学的荣光。
当年鲁迅就曾经在《论照相之类》中对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有过酷评:“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象一个麻姑。”现在人会觉得鲁迅太刻薄,对国粹京剧和梅兰芳本人有偏见。但是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对视觉表演艺术的不屑,对自己老本行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一个《红楼梦》粉丝对自己偶像的忠诚。
梅兰芳自己也谈到红楼戏难演:“前清光绪年间,北京只有票友们排过红楼戏。那时票房的组织还没有后来那么普遍发展。著名的有两个票房,一个在西城,叫‘翠峰庵’,名角如刘鸿声……他们排过‘葬花’和‘摔玉’。陈子芳扮黛玉。他的扮相是梳大头穿帔,如同花园赠金一类的小姐的打扮……每逢黛玉出场,台下往往起哄。甚至于满堂来个敞笑。观众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林黛玉……可是内行看了这种情形,对于排红楼戏便有了戒心。”
荷马史诗中写海伦的美,就说那些特洛伊德高望重的长老,本来对这个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女子充满怨念,但是他们在城头一看到海伦,就觉得为她打一仗也是值得的。再看看电影《特洛伊》中的海伦,那简直就是五大三粗啊。
我是个金庸武侠小说迷,但每次我看所谓的武侠电影里那些大侠们的死缠烂打,贴身肉搏,气度全无,犹如街头混混,都是无比失落。武侠小说是最需要打开人的想象力让人飞翔的,但这想象力投射建构的对象,一旦转换为银幕上的具象,就立刻跌落尘埃,猥琐暗淡。这可以称为武侠神髓的不可视化。
麦克卢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概念: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他认为文字相对于电影而言,属于低分辨率。低分辨率在这里不是贬义词,文学的低分辨,就像中国传统画的留白和写意,为欣赏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屏幕的形象固然直观生动鲜明,但语言创造的形象却更含蓄,更灵活,更能激活个体的想象力。“嘤咛”一声,需要多少高的比特率、采样位数和采样率才能表现?“吹弹得破”四个字,要用多高的分辨率才能表现?
那些电影难以表现之处,就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即使是在追求互动性的新媒体时代,文学也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当传统艺术中被压抑的交互性被技术激活释放,成为人民群众越来越大的渴望,缺乏交互性就会成为艺术的软肋。游戏的确比电影能带来更多玩家的选择,但文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能提供更高层次的互动———想象的互动。
文学不死,只是转型。人类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自己常用的一切媒介、符号和工具美学化、艺术化,也就是升华———用哲学的说法,就是异化。比如声音就升华成音乐,图像就升华成美术,哪怕是最实用的手机,也会不断增加超功利的审美因素。那么,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也就还会不断地升华语言,把语言艺术化,也就是文学化。电影电视的出现,反而让文学变得更加纯粹,并将继续成为影视、游戏、VR的灵魂。外壳可换,灵魂不灭。
(作者严锋,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护眼台灯”乱象调查
“护眼台灯”乱象调查 AI账号成起号新套路 多手段绕过“AI打标”背后有哪些隐患?
AI账号成起号新套路 多手段绕过“AI打标”背后有哪些隐患? 当心!你收到的赠品、小样可能暗藏猫腻
当心!你收到的赠品、小样可能暗藏猫腻 冲上热搜!“美的被曝强制18点20下班”,最新回应
冲上热搜!“美的被曝强制18点20下班”,最新回应